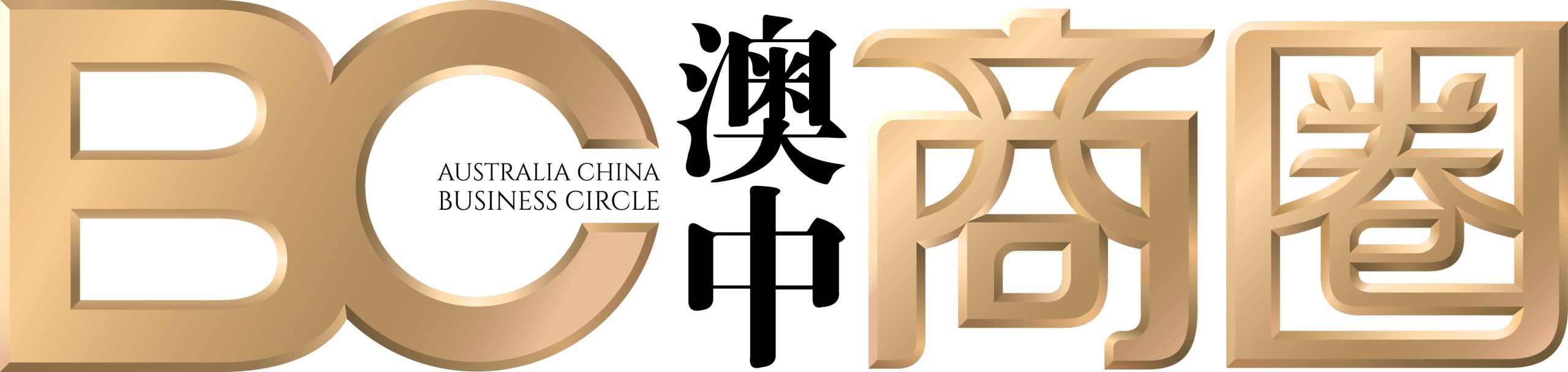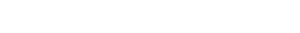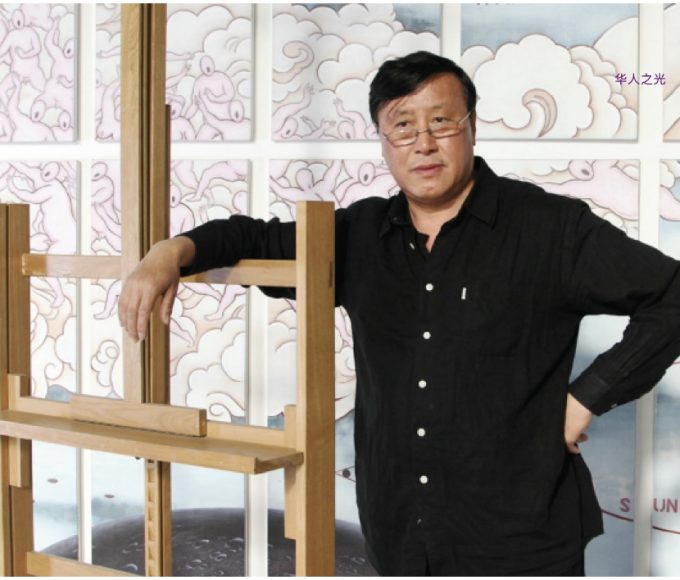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在高速公路上遇见特殊状况,不得不绕路,绕过一个口,发现还得绕行,再一个口,接一个口,不停地绕行,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一辈子就这么弯弯绕,永远迷失在路上。Detour是一个有趣的英文单词,剑桥英语词典解释说, 绕行通常是为了避开某个障碍,难免会走多点路。
九十年代的上海是大门正式打开的年代,我毅然辞去了政府公务员工作,不惜从父母那里借钱,赔偿了好几千元违约金,包括父母在内,所有人都认为我冒冒失失砸掉了金饭碗,但是,我想我知道需要什么,我的青年时代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可取之处的话,就是一点微弱的正义感和理想破灭后对现实的反抗。虽然我在大学期间发表了长篇翻译作品,但我还是放弃了文学梦。

商人
经数年蚂蚁搬家的努力,在德国我捕捉到一个机会,用环欧旅行的一个月,收购了德国汉堡的一间小型医材分销公司,剪除中间环节,成为少数几家雇佣德籍销售员直接把产品卖入德国医院的中国民营出口企业之一。一转身,我又逮住第二个机会,从意大利引入技术支持,在中国内地成立一家拥有十万级净化车间的医用耗材合资工厂,率先给欧洲客户制造装船前灭菌套装手术包,初步实现了产销一体化整合。
在两年时间内,我收回收购成本,产品不仅在德国具有知名度,还从德国转销西班牙、法国和北欧。当坐在上海浦东敞亮的现代化办公室内,面对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我开始幻想把一面面红旗插遍地图上每一个角落。未来似乎已经打包装进了一只坚固的出口包装箱。但是,未来是一阵风,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到听见风声,它已经去得老远老远……
一个意大利客户,我的一个老朋友,首先向我发出了忠告。他发现欧洲市场出现了不是从我司出口却打着我德国公司品牌的产品。骄傲和野心膨胀到我全然没有顾及市场上山寨版产品淹没了正品,全是产自我的国内合资工厂,订单却是来自另一间奇怪的新成立公司,与我德国公司同名。
同时,两位德国高层为了夺取公司,早已互相串通,将资产转入新公司,而将债务扔给老公司,任由其破产,好让新公司名正言顺接手销售管道,并从我的合资工厂采购。德国高层雇员——一个前南斯拉夫的共青团书记,开口闭口都是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的人,曾亲自飞到中国内地,说服我工厂合伙人与之连手,通过一系列秘密的“合法”程序将我踢出了新公司。
我陡然惊觉腹背受敌。当我焦头烂额不断投入资金,企图挽救德国公司财政时,我的商业帝国开始摇撼,发出吱嘎的解体声响。

我花费巨资请德国律师,发动了一场诉讼战争,不为了夺回德国公司,也要毁了它。哪怕是在欧洲的火车上,我都要忙着看讼词写文件。
记得那是在前往柏林的列车上,窗外飘着圣诞气息的大雪,转眼覆盖了德国乡村雪野上脚印,一夜间也染白了我的头发。在有节律的铁轨震荡声里,我心里翻江倒海。从德国医院直销先驱到被赶出这个市场,上帝的风极其高效,只用了四五年时间。刮倒我的不但有德国老朋友,也有中国合资工厂的两名合伙人和若干供货商。怀疑人生是一句肤浅的话,那时候的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不得不否定全世界。
牧师
当坐在地球另一端靠近南极的家里,看着蚂蚁旁若无人从花园爬进客厅,我想起数年前在北京的一件小事。
当时,我去北京出差,晚餐结束,大学时代的班长才姗姗来迟,他坐在那里,无心吃喝,问什么耽搁了,他说是在看蚂蚁搬家,看了居然有两三个小时,蚂蚁从这一头把家搬到那一头,他轻轻吹了一口气,蚂蚁们都回去了。几小时等于蚂蚁生命的几天几月几年白干了,而他花了十来年时间在北京娶妻生女,有房有车,但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他觉得自己就是宇宙中的一只蚂蚁,不知道哪阵风把他打回原形。
我发现蚂蚁的眼睛竟然看不见人。他们只是二维世界的动物,加上时间维度,充其量也就是三维动物,而这个世界按照数学家的演算就起码十维以上,多一维我们尚且不能理解,多七维八维该怎么办,圣经诗篇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以为这是我的地球,岂知这是那至高者的后花园。我绕行了世界一大圈,竟然又来到了《圣经》的话语面前。

绕行于我而言,没有避开上帝,而且遇见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东西。然而,遇见耶稣,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意味着你得把过去几十年积累搭建的违章建筑统统拆掉。我撤销了德国诉讼。
2011年是我人生中最为苦闷难熬的日子,在读经查考中,摩西和我一起流浪四十年,约舒亚和我一起跨过约旦河,进入流着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耶稣带我在棕榈日进入圣城。当我第一次开始向上帝祷告,怀疑是主要的动机。然而,神的信实一次又一次向我证实耶稣所说那种移山填海的力量。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不是停留在神学知识或祷告话语上,每一个都经过死荫幽谷,都有经历神的见证。每一个祷告都是信仰建造上的一块砖石。
那时候有三个发现冲垮了我对理性、对科学、对无神论的信仰:
其一,人虽有理性的追求,但从更为基本层面上看,却是非理性的。无神论完全没有证据或实验证明,实质上也是一种宗教;没有人生来是无神思想。实际上,大多数人在人类历史所有阶段都是有神论者,如果不是从小刻意在全方位灌输,一个人自然而然会产生的思想是有神论或不可知论;
其二,科学与宗教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彼此冲突。相反,许多证据表明科学起源与宗教密切相关。事实上,美术、音乐、文学、医学、天文、化学和物理等人类主要知识的起源均与宗教有关。科学仅仅有六百年历史,却几乎夺取了各个领域的话语权,以至于有人把它高举到几乎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地位。然而,科学对世界和人生的观察十分有限,对良心和道德束手无策。科学发现越多,由此产生的问题也越多;纵然(有组织)宗教在现代社会已经被边缘化,但信仰却从来没有边缘化。相反,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正在飞速发展。
其三,上帝的保守一直在我生命中,我发现对此最难的事不是相信,也不是灵修,而是感恩。很多人生于此长在此,对索取习以为常,终于灵性枯竭。从文化渊源看,中国人历来没有属灵(spirituality)这个概念,害怕各种形式的知识灌输,却又趋之若鹜把孩子送进各种培训班接受各种教育,为了不输在起跑在线。然而,从来没有一种声音出来说要培育孩子的灵性。时代的悲剧,莫过于谎言洗脑已经把人培养成灵性干枯的人,干枯的灵比干枯的手更可怕。
我受洗成为一种叫做基督徒的新人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一个只追求智慧和只相信个人奋斗的现代人成为基督徒,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必然是一个神迹。这种新人类不是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而是从此开始了试炼。洗礼那天,据说是那个中文堂第一次人数超过100人,牧师兴奋地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我说大概更多人是希望看一看这个人的脑袋是怎么漏进了水。

作家
做一个创业的商人需要勇气,做一个放弃商业的传道人更需要勇气,勇敢者的道路是绕行,但如此绕行必然也是神的恩典。我绕行了半辈子,以为已经聪明地避开了在历史背后的那股超然力量的支配,却不料那绕行的距离正是这支配者提前设计好的恩典之路。
五年神学院的装备恢复了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赋予我解剖自我与社会的手术刀,我又重新提笔写诗歌写小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者,连续获得了诗歌奖和散文奖。
在我被按立为牧师后,我常常想:在现实的灾难面前,信仰不是某种苍白的主张或脆弱的理论,圣经也不单单是某种世界观的洗礼,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祖先对世界超越物质肉体的那崇高力量和智慧的见证汇集,是一份给后世子孙更新属灵、重新做人的免费礼物,不要怕否定自己,背起每一个人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哪怕为此绕行一大圈,付出几十年光阴。

写作此文时,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在台湾付梓印刷,理当可以松一口气。
但是,右耳边响起澳洲丛林山火的哔哔啵啵,以及从北半球那座长江畔大城市传来的求救呼喊,许多人连夜携家带口逃离瘟疫之城,还有人趁机把口罩等防护用品涨价几十倍,那都是人类心底里真正的恐惧与贪婪。
左耳边却响起一个柔和谦卑的声音说,不要怕,跟随我!绕行远路不正是为了丰富你的人生,加深你的生命体验,给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神论者否定自己特制下数段奇异的旅程。